我在二十多年前是湘西农村的小鸭客。黑油油赤条条的四岁小肉身每天起得比太阳早,睡得比鸭子晚。
我最恨也最怕的人是村里一个名叫“富婆”的富农分子的丈夫—穷福佬。他见了任何人的鹅鸭下田吃稻谷都狂敲铜锣,狂喊狂叫,然后,生产队长就按穷福佬的记录罚工分。
因为怕他,我每天扛一根比我身子长五六倍不止的竹竿指挥鸭阵,鸭子队伍偏离正确路线,我就长鞭必及了。一次,鸭子正欲偷吃,我正路遇“保安”,一气一急一失控,竹竿敲昏一鸭子。心下不忍,脱下斗笠罩住昏鸭,砰砰砰几拍,鸭子“还阳”了。
富婆解放前是富农女儿,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穷福佬除了敲锣严肃,其他方面是吊儿郎当二百五,两人配在一起,过得日子清苦。大年三十,别人家杀鸡杀鸭,他们家则“杀”了许多红萝卜白萝卜。两人对坐,白水当酒,萝卜当肉。一个说,来,这块肥肉你吃。一个说,我不吃又白又肥的,吃块红烧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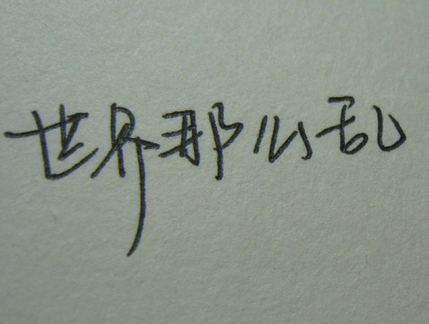

 网友点评
网友点评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