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把三十年代的一些非主流批评家如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梁宗岱、李长之等归纳为“京派批评”,其理由是他们表现出一些共同的文学观念和批评观念。且不说这种归纳是否有道理(因为任何文学观念相近的作家或批评家,我们都可以找出他们一些共同的东西,但这不能成为把他们作为具体的流派划分的理由),仅仅从关系上看,就很难说他们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流派。
他们既没有像左联、新月派、“现代”派甚至新感觉派那样表明自己群体性质的共同文学主张,也缺少属于群体性的共同的文学活动。他们的批评言论和活动都不过是自己个体的行为,缺乏流派所有的“共同体”性质。如果从更深层的文学思想来源与文学主张来看,这种“京派批评”说更难以成立。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梁宗岱,李长之等人的文学思想来源和文学见解之间的差距之大,使我们很难把他们纳人到一个统一的流派中来看待,除非我们现在关于“流派”的概念需要重新界定。更何况在所谓的“京派批评家”之外,还存在着像郁达夫、叶公超等这样一些同他们批评观念比较接近、批评方向也大致相同的批评家。
如果勉强归纳他们共同性的话,大概只能把他们同当时的主流文学批评相区别。而他们同主流文学批评之间的差别,其实不过是两种大范围的文学理念和批评理念之间的差别,并不是他们作为一个特别的批评流派存在的标志。我觉得研究这些非主流文学批评家,不必按照惯例非要给他们划圈子、分派别,而是要在确定他们存在特点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他们的个体性,从他们独具的个体性来看他们文学批评的意义和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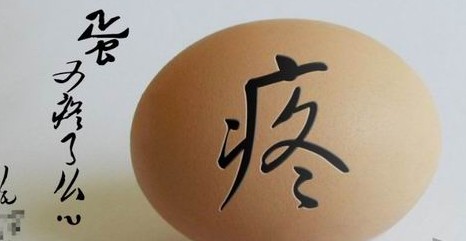
 网友点评
网友点评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