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更多偏重的是批评的理性特征和思想素质,左翼作家的社会厉史批评从马克思文艺观和现实主义理论出发,把批评主要看作是“生活的批评,社会的批评,思想的批评”,重视对作品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内涵的分析,并常以作家的思想立场和创作倾向来鉴别其创作的是非优劣。文化人生批评和新人文主义批评也是用固定的“思想法则”来作为批评的依据。前者标榜易卜生“健全的个人主义”,后者推崇白壁德抽象的“人的法则”;前者把批评解释为“科学的推论”,后者把批评解释为“严谨的判断”。
如梁实秋所言:“批评家需要的不是普遍的同情,而是公正的判断。批评的任务不是作文学作品的注解,而是作品价值的估定。”把“批评与艺术混为一谈者,乃是否认批评家判断力之重要,把批评家限于鉴赏者的地位。”他的意见代表了这两种批评的特色,即把对作品的思想分析和道德分析放在批评的首位,强调以一种超验的人性法则来厘定作品与作家。苏雪林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批评,梁实秋对左翼文学创作的批评,分别是这两种文学批评模式在批评实践方面的典型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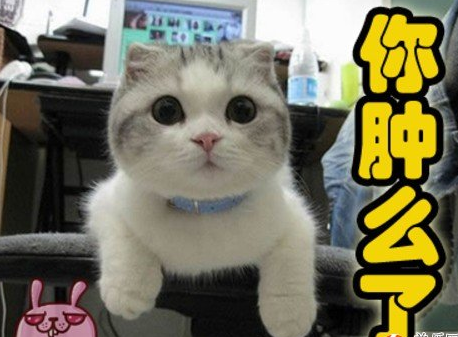
 网友点评
网友点评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