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对文学作“怎样写”的纯形式探讨,从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出发,对新文学进行具体的艺术理论建设,也是这时期非主流文学批评的突出特色。在这方面,它弥补了主流文学批评的疏漏与不足.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奠定了一块重要的基石。
尽管当时的主流文学批评在强调文学的社会特性与功利作用的同时,也对文学的艺术形式、艺术规律有过一些探讨和研究,如茅盾对小说创作技巧间题、周扬对人物形象的“典型化”间题、艾青对诗歌素质与形式问题等的论述都可以看作这方面的成绩,但从总的方面看,主流文学批评在这方面的建设是十分薄弱的。即使号称“新月派”头号批评家的梁实秋对关于文学“怎样写”的问题,也很少发表切实而具体的建设性意见。他的主要精力大部分用在了对当时文学“混乱”局面的指责、对“文学的纪律”的强调和对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问题的争论上.倒是在“新月派”不以批评见长的闻一多关于诗歌“格律化”的主张是这方面不多见的理论建树。
然而,在二十年代的非主流文学批评家们那里,对文学作“怎样写”的纯形式探讨则成为他们文学批评的一个重点的努力方向。郁达夫的《小说论》、《戏剧论》,朱光潜的《诗论》,梁宗岱的《诗与真》,叶公超的《论新诗》,老舍的《小说作法》,赵景深的《小说原理》等都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对文学形式探讨方面的特点主要在于,它们是从文学本体论的基本观念出发,注重在突出文学形式本体意义的基础上探讨形式的特质、构成及内部规律,而不是像多数主流文学批评家那样强调文学的社会意义对形式的决定作用,把形式仅仅看作社会性内容的“表现方式”,秉持的是一种内容和形式的二元论。它们采取的是内容与形式一体化或者说形式即内容的一元论文学观。在对形式的研究上使用的是虚化内容、强化形式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说具有“形式至上”的特点。如郁达夫认为,小说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的“艺术价值”,“小说在艺术上的价值,可以以真和美的两条件来决定。若一本小说写得真,写得美,那这小说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社会的价值,及伦理的价值,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尽可以不管。”他说,他的《小说论》的主要目的即在于“解剖”“小说的形式美”。
朱光潜的《诗论》的绝大部分内容也是专门探讨诗的形式问题:诗与散文在形式上的区别、诗的节奏与声韵、诗的形象性与绘画的异同、诗的格律等等。梁宗岱认为:“形式是一切文艺品永生的原理,只有形式能够保存精神底经营,因为只有形式能够抵抗时间底侵蚀。他把形式问题看作是诗歌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诗的本质就在于诗的形式,正是诗的各形式因素—节奏、声韵、意象、文字等构成了诗,构成了诗的诗意或诗境。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梁宗岱提出了“纯诗”的概念。他说:“所谓纯诗,便是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原素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而超度我们底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像音乐一样,它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它本身底音韵和色彩底密切混合便是它底固有的存在理由。”固然,非主流文学批评对文学形式问题的研究未必全然准确,其中自有它的偏颇之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执着于对文学纯形式的理论探讨对于加强新文学的艺术建设,减缓新文学先天具有的社会功利化倾向还是发挥了特定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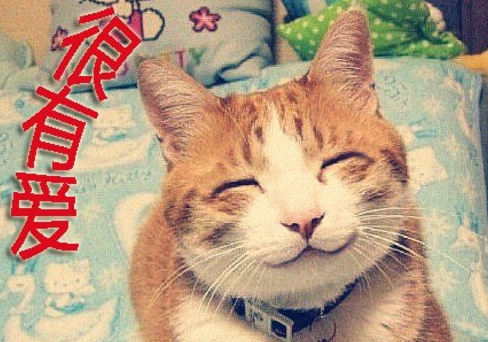

 网友点评
网友点评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