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语言的现象是复杂的。以词义而论,也不简单。碰到生疏的词儿,我们会查字典、辞典,最容易出岔子的,是碰到习见常用的词儿,自以为懂得,不加思索,便很可能象韩简和某同志那样只把自己所熟知的词义往上套,以致闹出笑话来。其实习见常用的词儿,词义也变化多端,同样忽视不得。同一个词儿,由于所处的语言环境不同,而引起用法有所区别的,就很常见。譬如同是“及”,《左传》里记嘻公三十三年“及诸(之于)河”,是指阳处父追赶孟明他们追到了黄河边。但《左传》里记阂公二年“及狄人”,却是指卫懿公被狄人追上了。同是“繁”,《文心雕龙·熔裁》里“张骏以为艾(谢艾)繁而不可删”的“繁”,是文字繁缛。但同篇“若情周(情理周密)而不繁”的“繁”,却指文字繁杂。这只是一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是由于时代的发展而词义发生了变化。譬如“烛”,《南史·沈彼之传》里“夜中诸厢廊然(燃)烛达旦”的“烛”,指的是蜡烛,但《韩非子·外储说》里“夜书(写),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日……”的“烛”,却是指火把。又同是“文章”一词,曹丕《典论·论文》里“盖文章经国之大业”的“文章”,和现在的意义一样;但《庄子,逍遥游》里“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的“文章”便指刺绣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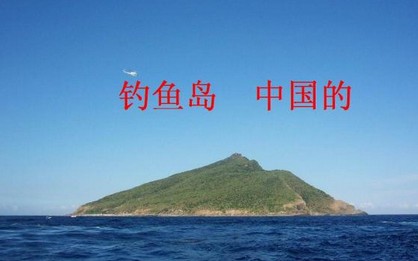

 网友点评
网友点评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