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译名的历史来说,音译的出现比意译更早。唐代开始作“骆驼”)、“猩猩”(又作“生生”、“牲牲”),在先秦的典籍当中已经出现了。而意译和音意并译则到汉代才有,前者如“胡桐”,后者如“酋长”。“酋”是羌胡语的译音,“长”是意译。但汉代的译名,用音译的占绝大多数。意译的译名到六朝才多起来。
音译一个词可以有好几种写法。如汉代从匈奴语音译过来的“琵琶”,原作“批把”,又作“批把”。今之“印度”,西汉时译作“身毒”或“天笃”,东汉时译作“天竺”或“天督”,唐代以后译作“贤豆”或“印度”。
音译的译名产生以后,为了便于使用,除了把不同的写法加以统一之外,古代还把它的音节或字数加以压缩。以中古时梵语的音译为例,有的删去开头一个音节,如“罗汉”即“阿罗汉”的简称。有的删去末尾一个音节,如“僧”即“僧伽”的简称。有的删去中间一个音节,如“夜叉”是“夜乞叉”的简称。有的删去中间和末尾一个音节,如“菩萨”是“菩提萨捶”的简称。有的斩头截尾,只留下中间一个音节,如“塔”是“数斗波”或“堵波”的简称,当然其中还经过简化为“兜婆”、“偷婆”或“塔婆”的过程,最后才简化为“塔”。简化工作不是任意进行的,这里面有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则可寻。如从梵语翻译过来的“璧流离”或“吠琉璃”、“毗琉璃”,有的省称为“璧泖(音留)”,有的又简化为“流离”或“馏璃”,最后还是从“玉”的“琉璃’,被群众批准,沿用至今。这其间是有道理的。原来这种译名虽非意译,但在文字上还是利用意符(即形符),表示了它的属类,自然容易得到群众的欢迎了。譬如“茉莉”,宋人、明人译作“末利”、“抹厉”、“抹利”、“没利”、“末丽”;但由于它是花名,所以明清以来,大家都爱用“草”字头的“茉莉”,就是这个道理。这和音意并译有点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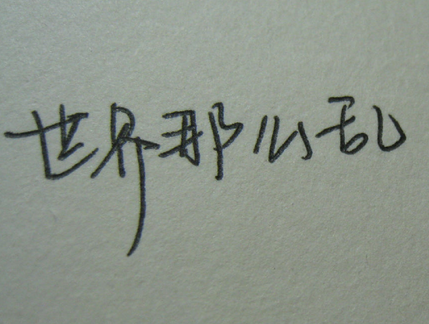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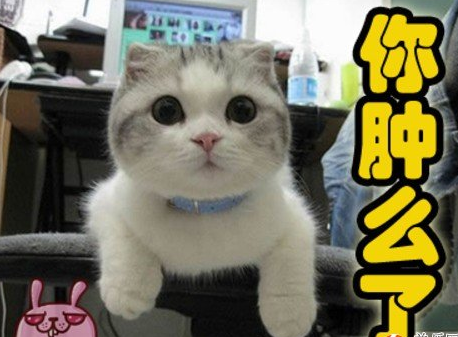
 网友点评
网友点评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