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文学批评从五四时期开始,其主流倾向就以倡导“为人生的文学”为起点。胡适、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等人所代表的社会人生派的批评,对郭沫若、成仿吾等人所代表的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派的批评,几乎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三十年代,这种现象仍然在继续,只是角色之间发生了转换与变化。郭沫若、成仿吾、郑振铎、沈雁冰进人左翼文学阵营,成为主流文学批评的骨干力量;周作人从“为人生”的殿堂避人为艺术的“苦雨斋”,变成了非主流文学批评家。
在自由主义文学批评内部,胡适继续执掌主流派文学批评的大旗,继续着五四文学的“启蒙’,批评话语。新加盟的是梁实秋,他的新人文主义批评在同左翼文学批评争夺话语权力的激烈论争中显示出了自由主义文学主流批评的特色。对于胡适、梁实秋等人的文学观念和批评观念,非主流文学批评具有不同的看法。李长之反对胡适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艺复兴”的说法,认为这场运动不过是一场“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主要特征,是理智的,实用的,破坏的,清浅的”,它所促动的文学革命主要代表了“启蒙”的功利要求,缺乏对文学本体上、美学上、艺术上的建设性。“有破坏而无建设,有现实而无理想,有清浅的理智而无深厚的情感,唯物,功利,甚而势利,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这那里是文艺复兴?尽量放大了尺寸,也不过是启蒙。”而同梁实秋的分歧更体现了非主流派文学批评与主流派文学批评之间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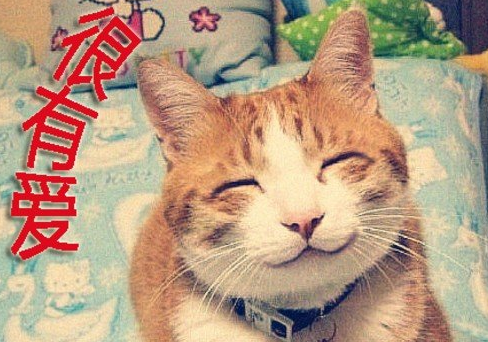

 网友点评
网友点评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